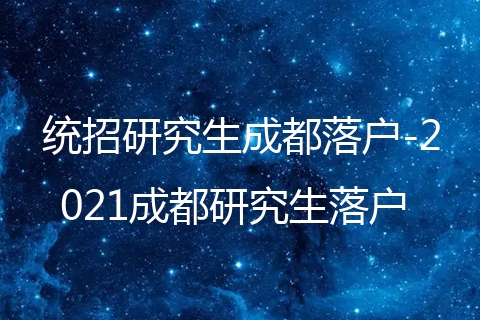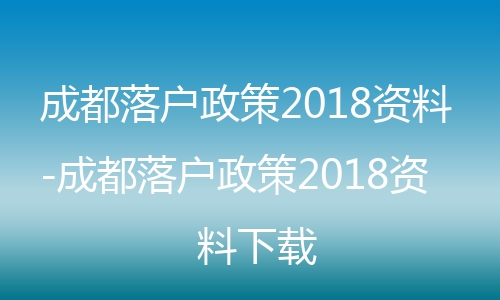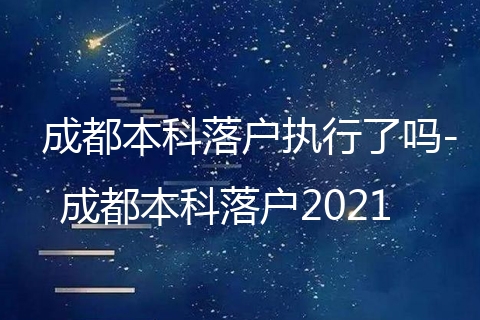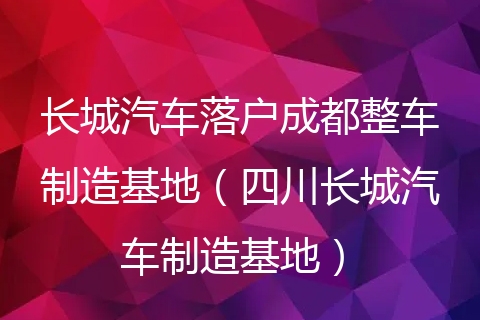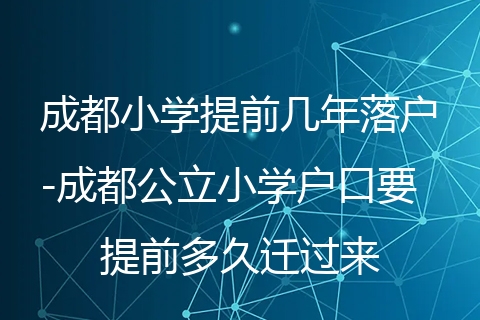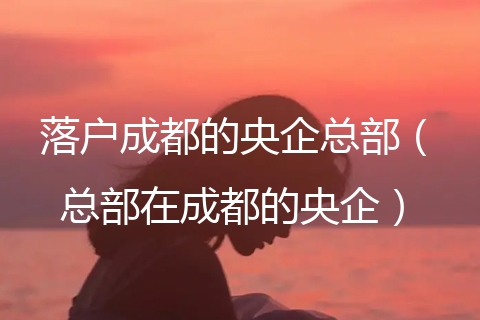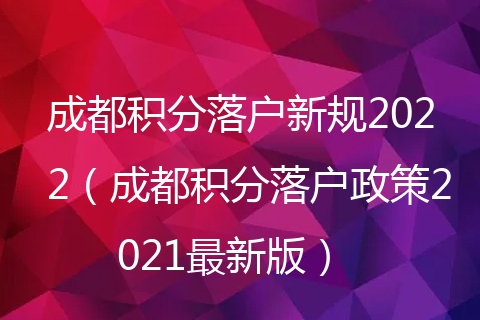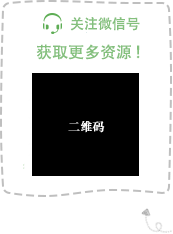格芯公司是哪个国家的
格芯公司是美国的。
格芯公司旅渣是一家半导体企业,全名为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桑尼维尔市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商,成立于2009年3月。格困卖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由AMD拆分而来、与阿联酋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和穆巴达拉发展公司(Mubadala)联合投资成立的半导体制造企业。
在2017年拆尺悄的时候,格芯公司也是在成都成立了12英寸晶圆成都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超过了90亿美元,产品应用在移动终端、物联网智能设备以及汽车电子等相关领域。
盲目投资全国造芯 芯片变芯骗
随着半导体行业获得政府和资本的青睐,全国各省正在掀起一场“造芯”运动,2020年上半年,已有21个省份落地的半导体项目超过140个,总投资额最少超过3070亿元。在2020年8月,就有近万家企业计划投身芯片行业,江苏、浙江、陕西、天津、辽宁、重庆、江西转产半导体企业数量分别增长了196.94%、547.37%、618.25%、465.31%、387.76%、422.73%和412.12%。截至2020年9月1日,中国已新设半导体企业7021间,2019年新设半导体企业也超过10000间。
在全国半导体项目遍地开花的表象下,潜藏了以下几点隐忧。
一是投资人动机不纯,芯片变“芯骗”。近年来,一些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理,套取国有资金扶持,结果钱没少花,芯片项目却没有多少进展,使地方政府蒙受巨额损失。这方面,武汉弘芯和济南泉芯是典型代表。武汉弘芯号称投资1280亿元,但实际到位资金却非常有限,从始至终大股东缺乏投资诚意,时至今日实缴资本依然为零,在武汉政府投入的真金白银烧光之后项目就陷入休克状态。同样的手法在济绝备南泉芯再度上演,在2020年2月,济南泉芯实际到位资金约5.1亿元,实际出资仍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与武汉弘芯如出一辙。
二是诱发官商勾结,带来腐败和权力寻租。当下,政府对半导体技术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海量国有资金涌向半导体行业。不少人就以不正当方式打通关节,获取高额国有资金大肆挥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淮半导体。德科码创始人利用在美国、日本求学、工作的背景,在南京、宁波、淮安三地开始公司,并套取海量国有资金。最终,号称投资30亿美元的南京德科码在2020年5月申请破产,宁波承兴半导体在获得700万政府资金后就没有后续了,德淮半导体烧钱46亿元之后无疾而终,地方政府为此冲兆背负了巨额债务。在整个过程中,腐败问题丛生。
三是技术引进贪大求洋,陪了夫人又折兵。当下,一些官员不善于培育本土企业,反而非常热衷于招商引资,寄希望于请“洋和尚”来念经,仿佛洋和尚念几句咒语,一个产业就能凭空变出来。面对一些跨国公司,瞬间就被迷花了眼,不惜血本高额投资,结果不仅没能引进技术,反而陪人夫人又折兵,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成都格芯和贵州华芯通。2017年,格罗方德与成都政府共同投资90亿美元建设一条12寸晶圆代工线。然而,巨额投资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成都格芯早已名存实亡,一直在寻找接盘者,只不过没人敢当白衣骑士。目前,晶圆厂里价值百亿元的设备只能放在那里积灰尘。贵州华芯通则是又一个惨烈的案例。2016年1月,贵州政府与高通合资成立华芯通,总投资18.5亿元,虽然华芯通高调标榜自主,但实际上,这款ARM服务器CPU就是高通ARM服务器CPU的马甲。由于ARM服务器CPU在商业市场上根本没有市场,众多曾经押宝ARM的厂商也难以为继,高通决定放弃ARM服务器CPU,在高通放弃ARM服务器CPU之后,华并判毁芯通就变成无根之木,自然而然也就关门了。
四是罔顾外部风险盲目投资害人害己。随着信创市场已经成为风口,为了进入信创市场和斩获更多市场份额,一些ARM阵营厂商不是以产品和服务为卖点,而是以政商关系为突破口,将“洋人地基上造房子”的技术包装成自主技术,在全国各地大肆搞圈地运动,向地方政府要政策和市场,搞单一来源采购。目前,C公司全国设立16家公司,H公司则与北京、天津、福州、厦门、成都、绵阳、重庆、上海、郑州、许昌、青岛、济南、合肥、西安、九江、南京、广州、深圳、东莞、南宁、太原、杭州、宁波、桐乡、武汉、长沙、醴陵、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城市签订协议,建立KP产业基地,从公司经营的角度看,C公司和KP在短时间内高频率的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建设产业基地是不太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这些子公司和产业基地大部分功能雷同,业务重叠,而且整机制造压根就不是高 科技 ,机关单位市场规模有限,这种规模的投产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前不久,随着外部环境越发严峻,H公司已经失去ARM芯片流片渠道,全国的KP产业基地面临缺芯的困局,生产能力和交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地方政府重金投资的整机厂几乎处于半休克状态。原本可以用来弥补芯片制造、设备、原材料等短板的资金,就这样被浪费在整机厂生产线上。
芯片产业是需要以十年磨一剑的方式细细打磨的,并非短期打鸡血就能够做成的。
目前,国内掀起的“造芯”运动是非理性的,很多投身“造芯”的企业不仅在技术积累上少的可怜,还存在动机不存的问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芯片是高投资、长周期的项目,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如今,全国各省发展半导体产业,只会把有限的力量分散,白白浪费了海量国有资金和时间。
从全球来看,美国半导体企业主要集中在硅谷,日本半导体产业集群位于九州硅岛,韩国半导体产业集群位于京畿道和忠清道,我国台湾省的半导体企业高度集中于新竹科学园区,都不存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情况。
技术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定,必须循序渐进,地方政府不要妄图短期用政策和国有资本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要妄图短期用行政资源砸出一个产业,方式方法不对,投入的资源越多,最终也只会鸡飞蛋打,南辕北辙。
当下,顶层应当加强对半导体产业的统筹,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规划和发展产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现有的产业特点进行布局,使设计、制造、设备、原材料、封装全产业链齐头并进。在国有资金的使用上,要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对于半导体产业扶持资金的发放进行严格审核。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把资金和时间用于扶持本土厂商中的“绩优股”和“潜力股”。

停摆17个月,建厂以来从未开工,成都百亿烂尾芯片项目或被接盘
作者|吴昕
停摆两年的烂尾半导体项目「成都格芯」终于迎来了接盘者。
据集微网报道,多位业内人士介绍,成都高真 科技 将接盘成都市政府为格芯投资70亿元建设的厂房,并在此基础上建设DRAM生产线。
格芯即格罗方德。2017年全球第二大晶圆制造厂商格罗方德,在成都正式启动建设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工厂建成后业务即接近停摆,2019年5月17日宣布关闭。
接手者成都高真 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28日,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衫档受益人崔珍奭是前SK海力士副会长、前三星电子技术开发部首席研究员。据悉,目前韩国仅有两名可以具备全半导体领域从研发到量产经验的元老,崔珍奭是其中之一。
DRAM芯片市场垄断程度极高,基本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瓜分,且竞争残酷,打压对手现象十分严重。我国DRAM芯片正处于从0到1的起步阶段,若接盘成功,对国内市场会是非常大的利好。
企查查资料显示,成都高真 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1.091亿元人民币,目前有两家股东:成都积体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6546亿元,持股60%;真芯(北京)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0.4364亿元,持股40%。
其中,成都积体成立于2020年9月28日,由成都高新区电子产局派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100%持股,实际受益人为NEXT创业空间CEO贺照峰。
真芯(北京)是崔珍奭的另一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14日,由西安市新隆宏鑫 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100%持股。
崔珍奭堪称韩国半导体界元老级人物,历任三星电子技术开发部首席研究员、常务理事和SK海力士半导体专务理事、副社长等,并在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
他从三星跳槽至SK海力士时是本世纪初,当时海力士濒临破产,崔珍奭带领手下技术团队在不到2年内将公司研发能力提升到与三星同等水平,使海力士起死回生,堪称韩国半导体发展史上的经典。
从可查询到的资料来看,崔珍奭对中国半导体市场有很大的兴趣,曾在2018年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韩国半导体业界已感受到中国的进步。虽然韩国企业规模更大,综合技术实力更强,但中国的步伐显然迈得更快。」
2019年,崔珍奭在中国成立真芯(北京)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企查查数据显示,真芯已经申请了43项晶圆制造相关专利,所有技术均为真芯半导体与中科院微电子合作研发,其中两项专利直接与DRAM芯片相关。
据集微网,真芯还引援了SK HAN、YH KOH两员大将,分别担任COO和CTO。SK HAN有着35年的半导体行业经验,曾担任三星制造部门9Line PJT长、SK海力士M8/M9制造部本部长。YH KOH则曾担任SK海力士NAND/MobileGraphic DRAM开发部门GM。
格罗方德宣布在成都建厂时,消息轰动了整个半导体界。
2017年、2018年前后正值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良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扶持政策,一时间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阵造芯热。
作为我国中西部重镇,成都已经吸引了英特尔、德州仪器、超微半导体、联发科、展讯等企业布局,形成了设计、制造、封测完整的产业链。
格芯在成都启动建设的是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工厂按计划分两期进行。一期12寸厂将从新加坡厂引入0.18/0.13μm工艺,预估2018年第四季投产;二期将导入22nm FD-SOI工艺,预估2019年第四季投产。
成都政府为格芯建厂投入70亿元,负责厂房、配套的建设和研发、运营、后勤团队的组建。但总投资规模累计超过10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是93亿美元,其余为基础设施和生态链建设。
与大多数晶圆制造公司用FinFET工艺不同,格芯选择的是FD-SOI工艺,设计制造成本更低,在物联网、可穿戴设备、 汽车 、网络基础设施与机器学习、消费类多媒体等领域都大有用处。
但FD-SOI工艺的发展受限于生或腊乱态系统不够完善,在IP建设、量产经验与应用推广上都不尽如人意。所以当时格芯就有意和成都政府一起建设FD-SOI生态链,希望中国的芯片设计公司能够采用SOI技术来迅速推动市场成熟。
格芯当时在全球运营11座晶圆厂(5座8寸,6座12寸),其中8寸晶圆厂有4座位于新加坡(原特许半导体),1座位于美国(原IBM);12寸晶圆厂有2座位于新加坡(原特许半导体,其中一座是8寸升级而来),2座位于美国(1座是原IBM),2座12寸位于德国(原AMD的FAB 36和FAB 38,现统称FAB1),工艺节点从0.6μm~14nm。
新加坡业务运营的总经理兼任成都工厂CEO,由于新加坡工厂负责人很多都是华裔,他们已经在准备用当地的客户、工艺、人才支持格芯成都起步。
不过,建厂两年不到格芯就停摆了。
2019年5月17日成都格芯下发了三份《关于人力资源优化政策及停工、停业的通知》。通知中,成都格芯称,「鉴于公司运营现状,公司将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正式停工、停业」。
而对于后续仅剩的74名员工的赔偿安排,该通知称,在2020年6月14日及以前离职的,格芯将按劳动合同规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6月15日及以后,按照不低于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
对于7月18日及以前合同到期的员工,格芯也将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N)。7月19日及以后合同到期的员工则能获得N+1的经济补偿,如果在2020年5月19日下午5:30以前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格芯还将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作为签约奖励。
烂尾现状和格芯母公司有脱不开的关系。
格芯最初是AMD的晶圆制造部门,因经营不善2008年AMD将其卖给了阿联酋的投资公司ATIC,重新组建后的公司就是现在的格芯。
此后的十年中格芯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晶圆制造工艺水平差、良率低,全靠母公司ATIC输血。创立以来,ATIC已经向格芯注资近300亿美元,但格芯净利润一直是负数。掌舵人也在不停更换,不到10年时间换了4任CEO。
成都建厂是第三任CEO Sanjay Jha的决定,格芯先是在2016年与重庆市政府谈判,但同年爆出大规模亏损,谈判未果,后与成都签约。Sanjay Jha发展战略比较激进,除了成都建厂,还新建纽约厂、收购IBM微电子业务、研发7nm,但在任期间亏损非常庞大,创下年均亏损超10亿美元的纪录。
第四任CEO Thomas Caulfield上任后开始大规模砍业务线,与中国的合作也改弦易辙。2018年6月,格芯全球裁员,成都厂招聘暂停;2018年10月,格芯与成都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修正案,取消了原计划从新加坡引进的180nm/130nm项目。
多方压力之下,格芯成都项目宣布关停。但厂房已经建好,因为设备价格太高且基础设施本身就有问题停摆近17个月无人接盘。如果高真 科技 成功接盘,对成都政府和国内芯片市场或许都是利好。
参考资料:
;news_id=761273